【学习园地】中国梦 求是路
发布日期:2014-09-30 供稿:中国教育报 编辑:新闻中心 辛嘉洋 阅读次数:
为了进一步促进集团建设,帮助广大教师、干部群体关注高等教育发展,了解行业发展前沿,拓宽视野,引发思考,党委宣传部特开辟“学习园地”专栏,为教职工推荐具有一定深度的新闻报道和理论思考。本周推荐刊载于中国教育报的《中国梦 求是路》一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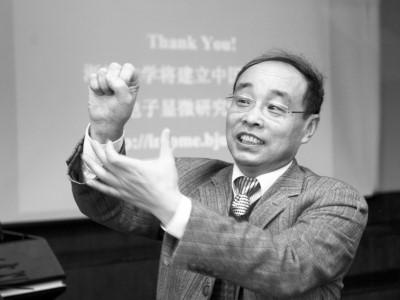

■张泽
——党委宣传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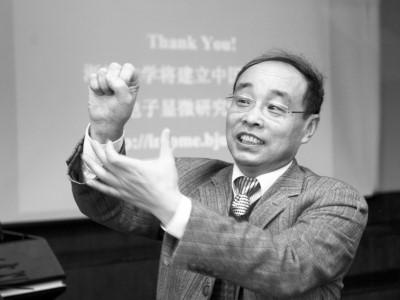
张泽,1953年生于天津,材料科学晶体结构专家,中国科我司院士,浙江大学材料系教授。1980年毕业于吉林大学物理系,1983年—1987年在中科院金属研究所,师从著名晶体物理学家郭可信院士,先后获得硕士、博士学位。2001年当选为中国科我司院士。全国政协第九届、第十届、第十一届委员。2012年2月,张泽院士被推选为新一届亚太显微学会理事长。
张泽院士长期从事准晶、低维纳米材料等电子显微结构研究,将原子层次显微结构分析与材料科学中重要问题相结合,系统研究解决了准晶、低维纳米材料等国际材料科学界的一些重要问题,取得了创造性研究成果。
自2010年3月起,张泽院士全职出任浙江大学材料系教授,组织和引领浙大乃至长三角地区高校电子显微结构领域的相关研究。现任国家重大基础研究(973)项目首席科学家。
“如果我们总在算计拿了多少经费、发了几篇文章、影响因子有多少,科学的方法一定不会产生,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的精神压根儿就会被放到一边去,那就不能形成崇尚科学的风气和风尚,更不用说是为了科学而献身的风气和风尚了”、“我们的中国梦一定是科学救国,一定是民主救国,而这种科学民主下的路一定是求是之路”……日前,材料科学晶体结构专家、中国科我司院士、浙江大学材料系教授张泽为浙江大学师生做了题为“中国梦 求是路”的学术报告。本报今天刊发张泽教授报告摘要,敬请关注。
■张泽
求是之路是通向中国梦的路
我的报告题目是“中国梦”,但这不是领导的命题作文。很长时间里,我一直在想,梦可以各种各样,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做,但是路的选择并不是。我们应该思考的,是我们自己的路、怎么样的路,才是和“中国梦”能产生关联的?我的思考结果——被关联的话题就是“求是路”。
今年是甲午年。两个甲子前的甲午年,中国和日本打了一仗,就是甲午战争,清政府大败。之后,签了一个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条约签下以后,中国的精英们——那些秀才发起了一个运动,就是1895年4月由康有为先生发动的公车上书。在北京的1300名应试的秀才不去赶考了,而要对国家的存亡发出声音,这应该说是中国精英们的一声怒吼。但直到三年之后,这种要求改革、要求变法的一系列声音才得到皇家的重视,这才有了一个戊戌变法。不过戊戌变法最后又是失败的,六君子死的死、跑的跑,谭嗣同被杀了,康有为、梁启超逃跑了。这一段历史就是当时没有成功的中国精英们求生存、求救国的运动。
在整个近代救国救亡历史中,最成功的知识分子救国运动应该是毛泽东开启的中国共产党救国求存的革命,这条路走得很成功。总结历史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一个思想路线。毛泽东不走城市包围农村的老套路,反其道而行之,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这当中的根本原因就是他一直坚持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就是指从实际对象出发,探求事物的内部联系及其发展的规律性,认识事物的本质。“实事求是”一词,最初出现于东汉史学家班固撰写的《汉书•河间献王传》,讲的是西汉景帝第三子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明朝王阳明提出了“知行合一”的观点,倡导“实事求是”的学风。
实事求是,这原本是一个经学和考据学的命题,也是中国古代学者治学治史的座右铭,现在成为了思想路线和科学精神的指称。而实事求是这件事本身和浙江大学也有着密切的联系。
众所周知,浙江大学的前身就是“求是书院”。浙江大学的成立是在甲午战争失败、戊戌变法之前。当时举国上下的一个思潮就是救国,而浙江大学就是在这个救国之路的探索中成立的,这条路就是“求是路”。当时的杭州知府林启向朝廷打了个报告,奏折里提出要建一个求是书院。求是书院应该说办得是非常成功的。当时在求是书院聚集了一批志士仁人,为了国家、为了民族尽自己的力,走一种新的道路,这条路是求是路。求是书院早期的学生,在当时救国救亡的运动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在教育、科学民主这两个主要的奋斗目标中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现在大家一提中国的近代教育史,就会讲蔡元培——北京大学的前校长。蔡元培先生是1916年准备述职上任、1917年正式上任的,他上任第一天所做的一个决定,就是邀请一个人。这个决定和邀请都是针对一位浙大人,这就是陈独秀。陈独秀因蔡元培的邀请到北京大学去做文我司的院长,而后陈独秀又请来了胡适、李大钊等,还包括鲁迅。一句话,就是没有“求是书院”的学生,就不会有“新文化运动”,也就很难想象后来的五四运动……
在中国近代的发展进程中,政界、军界、经济、文化各个领域,浙大的教师、浙大的学生都曾经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建国后第一任浙大校长马寅初先生,“两弹一星”的功臣赵九章先生、王淦昌先生,等等,太多了,不胜枚举。我想,这要归结为他们都选择了一条正确的路,就是求是路。
求是路西方人也在走。实事求是、按事实说话、为真理而斗争,这是西方文艺复兴以后的一曲主旋律。我举一个例子,就是第一位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伦琴,他在做校长的时候依旧亲自做科研。有一次伦琴做一个实验,把自己关在实验室里面,关了一个星期,因为他当时看到一个很重要的现象,他在开关仪器的时候发现了一种很奇怪的光,最终他把这个光追逐出来,因为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就称之X,就叫X光。这就是X射线的发现,全世界都轰动了,当时就有人向他来买,谈条件。第一个人是德国人,说要拿他自己的城堡和他的王位跟伦琴换。伦琴不要,伦琴说空气有没有价格?阳光有没有价格?我的科学发现就要像空气和阳光那样来为人类造福。这个发现在当时就知道以后会有非常大的利益,但是伦琴连专利都没有要。
反观今天,我们太物质主义了,我们太功利太自私了。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如果都这样的话,如果在戊戌变法之前,那1000多个举人不起来反抗的话,连戊戌变法都不会有,中国就出不了毛泽东,就不会有新文化运动。
没有思想的解放就不会有科学家
作为知识分子,要具有质疑的能力,不能不假思索地接受,这就是批判的态度、审核的态度,而这种态度对于我们今天的创新,对于我们的求是之路,都非常重要。
西方的科学技术之所以有今天,是因为科学家们用生命的代价,成功地反抗了教会的压迫。比如说哥白尼的日心说的提出,当时哥白尼已经有了明确的结论,写好了文章,就是不敢发表,只有等他死了之后才由他的学生和朋友发表。所以说没有思想的解放就不会有科学家,我再重复一遍,没有思想的解放就不会有科学家。布鲁诺大家更熟悉了,他非常支持哥白尼的日心说,最后却被教会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死前布鲁诺本有一次活下去的机会,教会说你只要认错,就放你的生。但是布鲁诺在真理面前宁愿赴死。这就是追求求是路的科学家们的价值观。
我们还可以说,怀疑一切,是求是的座右铭。马克思的创新精神就是源自他对人类文化遗产的批判。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都是批判继承与理论创新相结合的典范。马克思在青年时期曾经是狂热的黑格尔的信徒,在他发现黑格尔哲学体系中的矛盾之后,勇敢地提出质疑,并深入研究,最终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哲学中的唯心主义体系,吸取了他的辩证法的“合理内核”,以及批判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唯心史观,吸收了他的唯物主义“基本内核”,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的另外两个主要组成部分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也都是在批判地继承前人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创立的。黑格尔、费尔巴哈、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人都是思想理论界的权威,如果马克思迷信理论权威,没有敢于“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的勇气,没有敢于创新的意识,他就不可能创立马克思主义。
所以,今天的教授们不要不假思索去遵从权威,不管他是学术的、政治的还是宗教的,不要不假思索地去遵从社会的习惯,要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用自己的头脑想问题,要关注事实本身。
爱因斯坦1905年写了三篇文章,这三篇我觉得都非常好,当时大家公认都可以拿诺贝尔奖,一个是光电效应,一个是相对论,一个是布朗运动。这三个科学发现中哪个都可以得诺贝尔奖,最后得诺贝尔奖的是光电效应,是1921年的诺贝尔物理奖。而事实上,诺贝尔奖1921年的奖项是空缺的,是1922年补了前一年的奖。自爱因斯坦发表那些文章之后,大家马上就认为这是非常有创新性的成果,应该得诺贝尔奖,但实际年年都没给。而爱因斯坦的回答是什么呢?他的回答是:我对科学的追求像宗教一样。他写过的一篇文章《科学与宗教》中说,“人类进步的精神进化越是深入,我就越坚信通向真正的宗教之路不在于对生命和死亡的恐惧之中,也不存在于盲目信仰之中,而在于对理性知识的努力追求之中”。
如果仅仅是为了像我们现在算工分一样做科学,总在算计“拿了多少经费”、“发了几篇文章”、“影响因子有多少”,是不可能把科学事业做到如此之辉煌的。在科学发展历程中,什么最重要?还是理想的追求,这才是最重要的。
怎么能够求实、求是?西方的科学家包括艺术家,作出了很好的表率。达芬奇就是个大艺术家,《永恒的微笑》能笑这么多年,这个微笑的背后是科学,是达芬奇对人体透彻的了解。只有在这样一种透彻的理解之上,包括对骨骼的解剖学基础的了解,才会有当时西方绘画艺术的真,包括真实的透视感。林语堂就曾评价说,西方的风景画,画的是透视,中国的山水画,画的是写意、大泼墨。仔细想一想,真是这样,西方绘画有焦点、有透视;中国绘画讲意境,视点散射,无透视。那时西方的画是非常讲究比例、讲究几何甚至讲究解剖的。这种现象的背后,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大艺术家们对自然现象和人本身的关注,这是西方学者们共同的追求。而中国受两千多年的封建政治影响,传统的知识分子多崇尚儒教,想的是入朝为官——“学而优则仕”,注重的是人际关系,“四书”、“五经”等著说皆重于此。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社会不重视科技,认为是雕虫小技,不屑于学习,不仅科学知识不能普及,科学方法、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也不能蔚然成风。周光召先生就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中国“未能做官或官场失意的知识分子,多舞文弄墨,钻研故纸,或归隐田园,或放荡不羁,虽留下千古文章和诗句,除个别人外,都不去从事对自然界的了解和研究”。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有它辉煌的东西,有它好的一面,但是真正影响国家发展的又确确实实就是这些。所以求是和创新在中国的文化层面上遇到了极大的障碍。中国传统文化中这些糟粕的东西确实应该引起我们知识界精英,特别是今天的教授们注意。如果太注重那些东西,科学的方法不会产生,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的精神压根儿就会被放到一边去,那就不能形成崇尚科学的风气和风尚,更不用说是为了科学而献身的风气和风尚了。
文艺复兴,复兴的不是文艺,复兴的是价值观。神权至上中很关键的理论就是地心说。地心说,太阳从东边升起,西边下去,貌似都围着地球转,这是大家都看得见的事实,而且上帝就是这么说的,这就是真理,谁说这是错的,就要杀头。但在神权至上的统治时期,依然出了伽利略、出了布鲁诺,最后诞生了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诞生了严格的公式,各颗星星之间,乃至所有物体之间的引力,都可以用公式计算出来。这不是靠革命、不是靠一个王朝去推翻一个王朝,不是靠一个理论去推翻一个理论,它靠事实、靠科学,这从根本上动摇了神权至上。事实证明,没有科学就不会有民主,科学和民主,一定是一对孪生兄弟。
求是——中国科学家的中国梦
中国科学家的中国梦,我坚信,一定是求是路,不走求是路,就不可能实现。我们的老校长竺可桢先生在1935年8月有过一篇讲演《利害与是非》,他指出,中国近30年来提倡“科学救国”,但只看重西方科学带来的物质文明,却没有培养适合科学生长的科学精神。他说“科学精神就是‘只问是非,不计利害’。这就是说只求真理,不管个人的利害,有了这种科学的精神,然后才能够有科学的存在”。老校长说的这个现象,在今天仍然改变不大,我们看的还是西方那些物质文明的成果,计算机、信息产业、网络等。对所谓现代化的理解,还只是停留在西方的科学带来的物质文明上,仍然没有关注到适合科学生长、发展的精神需要的空气和营养。竺可桢先生说科学精神就是“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现在对我们来讲,这个要求实在太高,我们都做不到。
浙大玉泉校区东侧有一个小桥门,门前小桥旁边有一个人行道,还有红绿灯,但红绿灯亮起来的时候,只能对大多数开汽车的人起作用,而那些骑电动车的人,我在这里过往了四年,就没有看到过一辆遵守这个红灯的电动车。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都不能够去遵守,要建立一个现代文明的国家,我看是不可能的。我们看到的所谓现代化,依旧是汽车、电动车、飞机等物质文明,但是最基本的东西缺失很多。所以今天在校园里面要强调科学的精神,至少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没有这些尊重,很多事情都不堪回首。有了科学的精神,然后才能有科学的存在,浙大的前辈们在这方面做得很好。
所以我们现在应该认真地去思考,1946年浙大7个我司25个系2100名学生,诞生了51位两院院士,而我们今天有7个学部37个院系4万多名学生,我们怎么才能够做得更好?我们要走什么样的路?我们存在的问题在哪里?
竺可桢先生讲大学教育目标是培养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会、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他的这个目标是很高的,我觉得现在我们的目标比这个要低得多。竺可桢先生说——大学本来不是传授现成知识的,而重在开辟基本的路径,提供获取知识的方法,并且培养学生批判和反省的精神。美国大学也是一样的,要让学者有主动求知和不断研究的能力。这才是大学要做的教育,这才是我们要培养的人才。
可敬的是在20世纪40年代中国那样的环境下,浙大做得非常好。当时浙大在自然杂志上的文章之多,令我们汗颜。我在这里想强调的就是——我们的中国梦一定是科学救国,一定是民主救国,而这种科学民主下的路一定是求是之路。
【观点交锋】
青年教师提问:刚才您有一张图片,表现的是牛顿在为民众讲解万有引力。牛顿只比他的受苦受难的前辈们晚了50多年,那么西方对科学的态度的转变为什么那么快?
张泽:我觉得这个应该归功于文艺复兴。“文艺复兴”复兴的不只是文艺,我认为,复兴的是价值观。从伽利略、布鲁诺,到牛顿,依靠科学,从根本上给了神权至上最后一击,社会所崇尚的价值观,从过去的以神为中心,到以自然探索为中心、以真理探索为中心。但中国的皇权崇拜,产生的绝对遵从的思想,违上大逆不道的思想,是根深蒂固的。所以我们至今还没有形成对科学技术的尊重。在我们的周围,甚至存在着将自然科学技术研究与人文社会科学对立起来的观点和行为。科学与民主,一定是一对孪生兄弟。现代中国,要走出几千年封建王朝的阴影,我觉得青年教授们要担当大任,你们要准备好。如果我们的眼睛就盯着自己鼻尖那点小事,我们怎么可能引领文化?怎么可能培养优秀学生?
青年教师提问:您怎么看待今天学生把老师当“老板”?
张泽:前两天有人问我“你对导师压榨学生怎么看”,我十分反感这样的说法。我不否认有些老师对学生不够尊重,甚至把学生当劳动力,这样的情况确实有。但这个现象要从文化的层面分析。首先,我们搞科学研究的,要把这个量化搞清楚,不能用0.1%去代表99.9%。其次,要建立相互尊重的学术环境。要诉苦抱怨的话,都有可抱怨的。比如有的老师评不上教授,他就觉得我早该当教授了,为什么我评不上?你们就是搞不正之风,就是如何如何。校长也一肚子委屈,只是不说。所以在经济富裕起来的前提下,在有了温饱和尊严的前提下,我们还真要好好在文化层次上修炼我们自己,建立起在学术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的交流,我觉得这很重要。否则的话,学生抱怨老师,老师抱怨领导;文科的看不起工程的,工程的看不起基础的……怎么相互尊重、相互欣赏?怎么建立共同的目标?把集团办好,这才是最大的工程。





